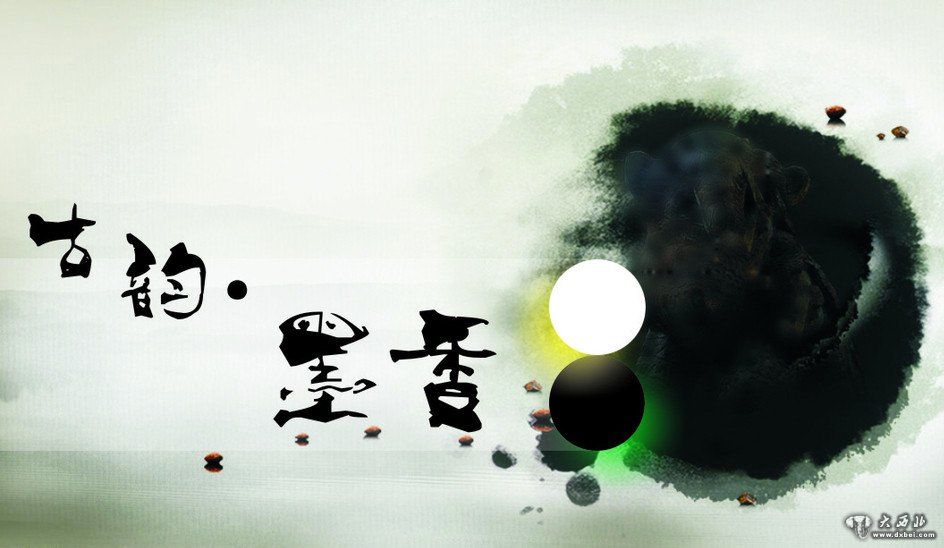
从我们镇南去三华里有座桥--宽不过数米,长不足百步--青石砌就,水泥勾缝,久经岁月,早已是一副不堪重负、不胜风雨的样子。桥下一脉细流,缓缓西来,潺潺东去,唱着一支永远不知疲倦的歌。这歌常常会在静夜里轻叩我思念父亲的心扉……
父亲一生爱字,早年多有题刻,可惜现在大都散湮殆尽,惟存这桥上30余字,算是留给我们的一笔惟一珍贵的遗产--作为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印迹,一代伟人毛泽东那"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雄壮诗句,早已随父亲遒劲的腕力刻进我心灵的版图--前些年,我和哥哥无论谁回乡探亲,途经这里,总要停下匆匆的脚步,在此久久徘徊,不忍轻易离去。两个同样的游子,用不一样的沾满异乡风尘的手,一遍遍抚摸着那秀逸的"柳体",仿佛触摸到父亲冰凉而温热的脸颜,心中隐忍的痛楚,一点点袭来,一点点上升,一点点蔓延和扩大--我们那曾经丈量过许多山川河流的双腿,却怎么都难以跨越眼前这座乡村小桥……
这是母亲为我们复活的父亲--
他在童蒙初开时,即受到了严格的家训。大约四五岁光景,就在祖父的督促下,过早地走进无情的童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尔后背诗,饭毕习字--不准坐,站着临帖--一炷香之后,方得解脱。这种严酷的家教结果是,父亲姐弟6人中,出了两个大学生,4个中师生。一时满门书香,让开封老家的爷奶赚足了喝彩和赞美。
青年时的父亲血是热的,不顾祖父的实木拐杖,执意投笔从戎,后因眼疾回乡执教,桃李何止三千?中年时的父亲依然书生意气,因而获赠"右派"帽子一顶,终于郁郁寡欢,刚知"天命",就因心脏病突发,高大的身躯猝然倒下--戛然而止的生命的琴弦,不知该留下几多怅恨和牵挂?
这是我童年眼中面影依稀的父亲--
他有时眉头紧皱,面色凝重;他有时朗声大笑,天真得孩子般前俯后仰……每年一进入腊月边儿,他常常是自己饿着肚子,为乡亲们提供那个年代另一种同样稀缺的"粮食"--用已经很成熟的"柳体",义务给他们撰写"中堂"和春联。而他最后所得到的报酬往往是:倒陪了许多瓶墨汁,磨秃了许多枝毛笔。他不在乎,他很高兴,也很感谢--感谢人家免费为他提供了练笔的纸张。他竟是这样一个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孩子般缺少心计和盘算的人,一个有着一颗透明的心的人--这个人一走,就是30多年……
但这个人的一缕墨香还在,除了一部分被岁月永久收藏,不再归还,更多的至今还芳菲在故里乡亲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