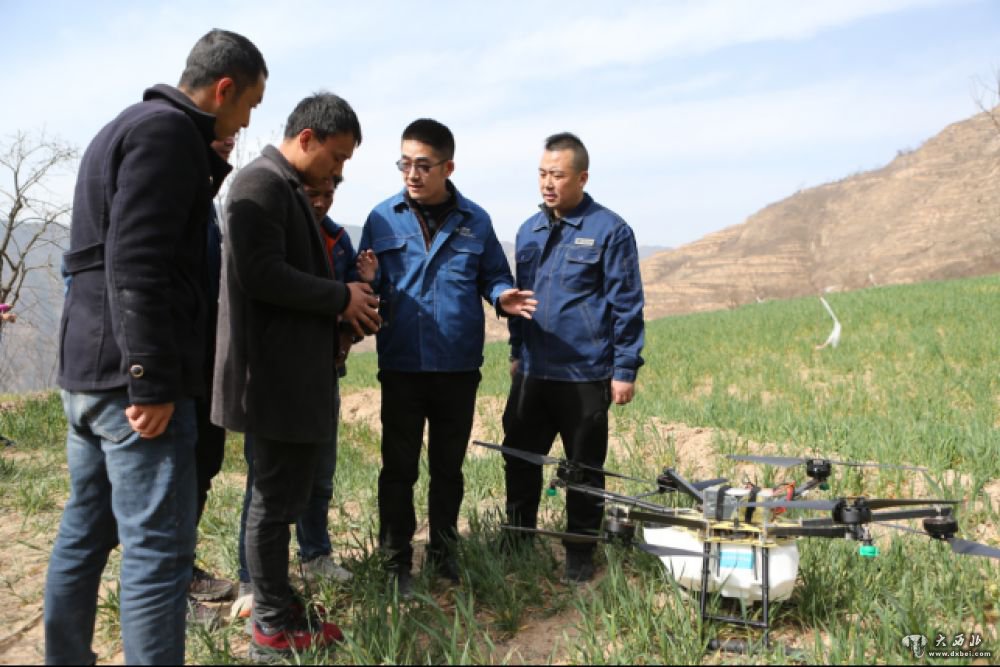2009年夏天,我第一次走进这校园。教研室主任打开一本《大学物理》,随手翻到“高斯定理”这一章,让我准备二十分钟,然后讲一节课。
四十五分钟后,我成了这所大学的教师。
后来我才知道,几乎每一年每一个来面试的人,讲的都是“高斯定理”.我们都被主任那“随手”一翻的风情欺骗了。用专业术语来说,本以为是随机误差,没想到是系统误差。
按规定,新教师必须听满一学期的课才能上讲台。那时我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以为上课不过如此。我曾在主任的课上,坐在最后一排,隐藏在一个胖子身后,酣畅淋漓地睡了两节课。然后擦擦口水,恬不知耻地跑上讲台,伸出大拇指,谄媚地说,主任,课上得真好呀!
主任斜了我一眼,抽出一张纸,上面是一系列数字--12、25、47、61……
主任慢悠悠地说,第一节课,从第十二分钟起,你开始睡觉。
第二十五分钟,你醒过一次,换个姿势接着睡。
一下课你就醒了,不知跑哪里去。第二节课,你迟到了两分钟,坐下就睡……
……
我一身冷汗。事后去厕所洗脸,发现额头上赫然一大片印堂红。
于是,我又多听了一学期的课。直到2010-2011学年,才遇见你们,我的第一届学生。
第一节课就差点迟到。我一身户外装束,背着登山包直接上了讲台,听见台下有人惊呼。那一刻,我感慨万千--原来站在讲台上看最后一排,是如此的清晰。
因为心虚,我像个笨拙地用小礼物讨女友欢心的男生,企图用段子吸引你们的注意力,或是唤醒后排酣睡的兄弟--讲我学物理的不堪过往,苦逼漫长的光棍岁月,或是一个人背包的旅途。见你们笑得很开心,这才有勇气把课讲下去:牛顿、法拉第、拉普拉斯、麦克斯韦、爱因斯坦……
一天,某位专家来听课,旁边的男生不知道是不是神经过于大条,居然很客气地对专家说:“我先睡会,待会路明讲笑话的时候叫我。”
还有位同学,直接在评教网站写,“以后有人问,你物理是语文老师教的吗?我大概可以回答,有过一任。”
总算,第一个学期上完了。答疑,考试,批了整整两天考卷。一位老师在复核的时候提醒我:“这位同学的分数好像加错了。”
那个夏天我去了伊犁。在那拉提草原,眼见一群小伙子横刀跑马,彪悍异常。突然,其中一个小伙子策马奔来,老远就喊:“你是……教物理的路明吗?”
我惊呆了,难道这就是桃李满天下的感觉吗?在那一刻,我坚定了一辈子当一名人民教师的信念。
我努力克制内心的得瑟,矜持地回答,正是在下。
小伙子转身朝他的同伴吼,就是他!就是他!
就是他让我挂的!
又是一学期匆匆而过。我想,我还是适合当老师,虽然有时讲着讲着会把自己绕进去,或者讲了一大半才发现讲错了。有一次实在收不了场,我冷汗涔涔下,心中有一万只蝎子精咆哮,“哇呀呀呀呀,这可如何是好?”
现在好了。我可以脸不红心不跳,带着鞠萍姐姐那样亲切和蔼的笑容,做钓鱼执法状,“小朋友们,看看刚才的解法有什么问题?”“啊呀呀,这么明显的错误,居然没有小朋友指出来,老师很失望啊。”
最后一节课,我对你们说,你们是我的第一届学生,就像初恋一样。
给你们讲过的题,下一届我还会再讲;给你们说过的段子,明年我还接着说。但那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再也不会备课到深夜,再也不会为一张图花一下午时间,再也不会上讲台前深呼吸,再也不会讲完一道题转身向黑板,对自己悄悄说,耶。
我在微博上写过一段话:男生应该学点物理。爬山时感受势能,游泳时思考反作用力,在篮球场练习抛物运动,在健身房复习热功转换,斗转星移验证了角动量守恒,世事无常的背后是测不准原理,在父母的皱纹中读出了熵增,在离别的时刻懂得了楞次定律。
是你们,在我讲错的时候假装没听懂,在我磕绊的时候给我足够的包容。与你们相处的日子里,我逐渐站稳了讲台。可我总觉得亏欠你们,给你们上的课不够好,却没有机会再来一次。
原谅我,初恋的时候不懂爱情。
你们要走了,从此各奔前程。我想我应该表现得淡定一点、冷峻一点,像个老教师的样子。你懂的,楞次定律。据《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