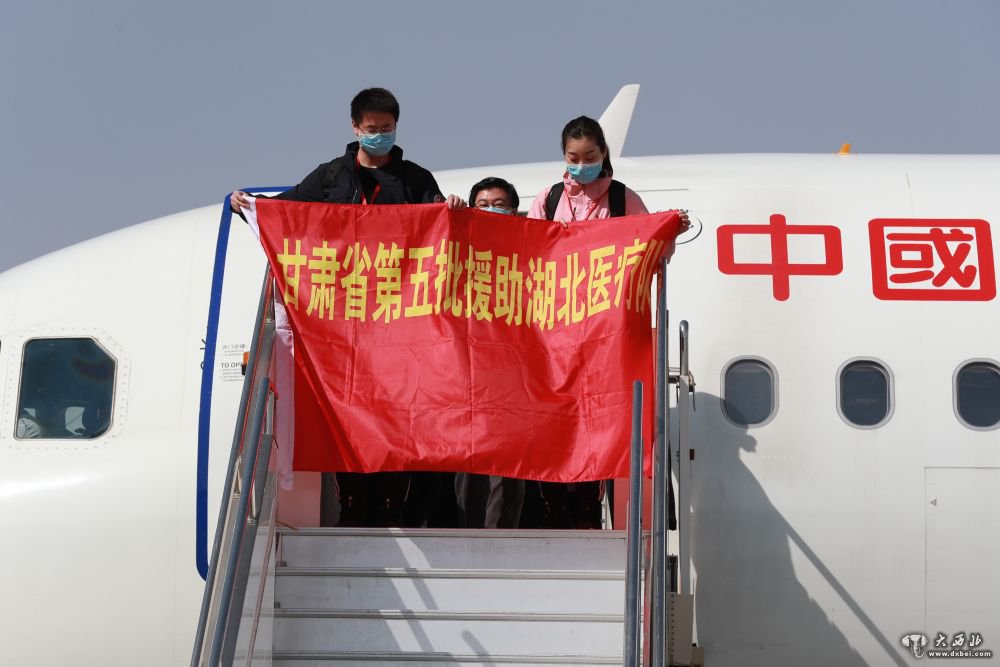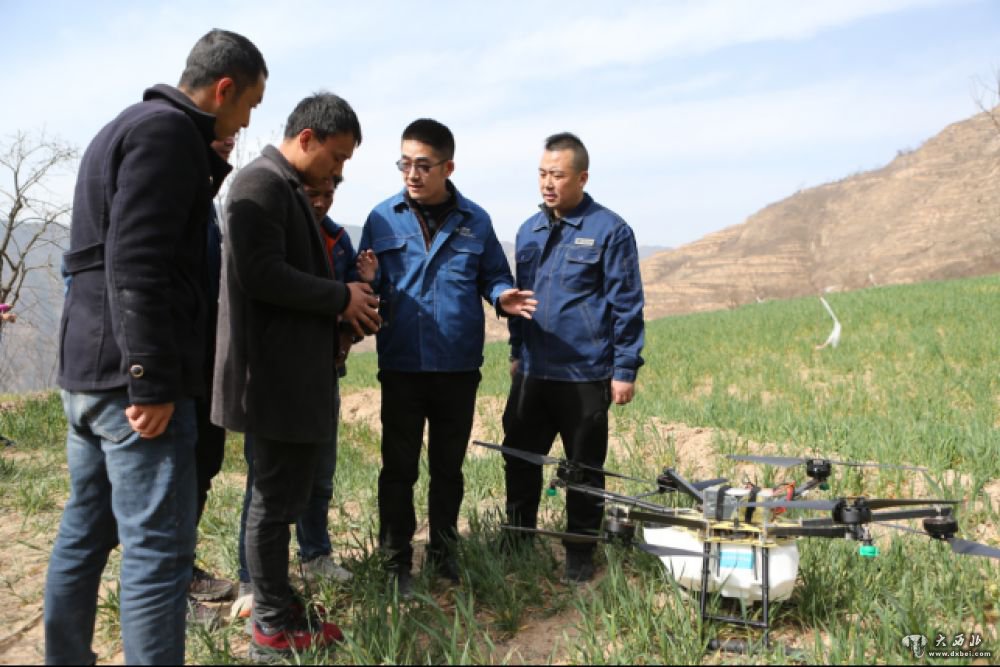姥爷那年16岁。
16岁的姥爷为人随和,人们有啥事总乐意叫上他。
那年过年前,三十多里外的刘庄有个大集,听说还有县剧团搭台唱戏,村里好些年轻人都赶去看热闹,姥爷也随人去了。回来时,姥爷跟四个哥哥辈的人说说笑笑地一起走。谁知走着走着,天就变脸了,先是刮起呜呜的北风,卷得尘土细沙飞扬,落叶碎草漫天,人都没法睁眼。紧接着,云就像从天边赶来的羊群,忽地从挤挤拥拥到一下铺开,眼看着就到了头顶,铺满整个天,并且越积越厚,越压越低。又一阵更猛的刀子风吹来,先乒乒乓乓地砸了一地冰珠子,接着就散散落落地下起了雪,越下越大,越下越密。
年龄最大的二柱哆嗦着一声喊:“雪怕是要下疯了,咱不能再走大道,太远,抄近道吧!”大伙一声应,想也没想,就抱着脑袋缩着脖子蹿上了山间小路。
山里的雪似乎小点儿,可谷里的风却特别厉害,劈头盖脸地吹,一阵紧似一阵,鬼哭狼嚎般响,刮得人都跌跌撞撞站不稳脚,吹在身上,更是刀割锥刺样疼。五个人没走多久就支持不住了。“不能再走了,快找个地方避避!”二柱大模大样地喊。“前面沟边有个小山洞,爹领我来过,咱到那去。”风里,三柱紧捂耳朵缩着脖闷闷地应了一声。大伙就跟着三柱往前蹿。
山洞寻到了,很浅,很窄,很矮,五个人进去就快挤满了。不过,洞里不仅没风没雪,出奇的暖和,更让人惊喜不已的是,不知何人在里面放了一捆干树枝。小火一点,就别提有多美多舒坦了。风却刮得更紧,大团大团的雪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直直往下掉,小道一下就被掩住了,看不清了。
“二柱哥,咱还是趁早走吧,不能歇,歇了怕就走不出去了。”一向不大爱说话的丫头站在洞口,看着满天风雪突然说。丫头当然是个小子,他爹老来得子,怕不好养,就给他取了个“贱名”.二柱一向看不起丫头,嫌他没爷们儿气,这回见丫头跟他唱反调,顿时很不高兴,马上拉下脸来:“你要怕死,你就自个儿走吧。”“二柱哥,天真不对,雪只怕越下越大……”丫头结结巴巴地说,急得都冒汗珠子了,“我看咱们还是赶紧走吧。”二柱手一甩,不让丫头往下说:“要走你走,没人拦你,我们都不走。”这时,一直没吭声的姥爷开了口,他说:“丫头哥说得对,咱是该走,而且马上走才对。”显然,没人料到一向顺从的姥爷会说出这样的话,大伙顿时都静了、愣了。二柱却突然发起了牛脾气,说啥也不走了。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谁也不能再说啥了,就僵着。丫头终于一跺脚,扭头看看姥爷,拧身钻入呼啸的风雪中。姥爷看一眼那哥儿三个,说声“那我和丫头哥先走了”,毫不迟疑地也随着闯进厉风暴雪里。
两人顶风斗雪跌跌撞撞回到村,已是上灯时分,都冻成了冰人,腿打不得弯,话说不出来。
那夜,气温骤降,滴水成冰,奇冷奇冷。大风呼呼地一直没歇过,大雪一直刷刷地没停过,直到第二天晌午风雪才稍稍小了点儿。村里的人着没大腿肚子的深雪,随着姥爷和丫头到山里找人。
山里的树上都压着厚厚的雪,小树都压趴了压没了,山崖上挂着粗粗的冰柱,沟里的溪水冻得结结实实,有的大石头都冻裂了,脚一蹬就碎。好不容易摸到那山洞前,洞口却给雪堵住了,扒开后只见洞里四壁上也全是冰霜,那点儿柴早烧光了,3个人抱在一起,都冻死了。
那回,姥爷在告诉我这个故事后,还特意加上了一句,他说,人哪,有时候就是一种选择哩,跟人咬咬牙往外闯,也许就挺过来了,活下去了,而顾顾情面,图一时安逸,缩一缩,就完蛋了。一辈子生活在东北山村的姥爷,是在88岁的高龄上去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