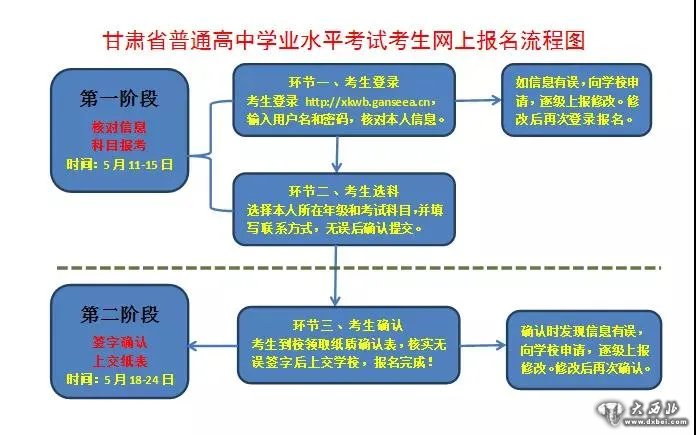在草湖人的美食印象中,柴火灶闷野兔、风干兔肉、红柳烤野鱼、辣子蒜头呱呱鸡……那些奔走行进中姿态轻盈、活泼跳跃的野兔,芦苇塘子里鲜活娇小的白鲢、鲫鱼,亦或是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呆头呆脑的呱呱鸡,或炖煮或干煸,或清蒸或红卤,是一代代垦边人童年里缭绕着的、挥之不去的味道。
草湖又称塔里木乡,位于新疆库车县城东南两百多里,面积八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不足六千,汉族群众约占六分之一,为支边青年以及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少数民族群众多为土生土长,再就是零星婚嫁迁至。
早些年交通不便,从乡里到城上,路是泥土路,赶着毛驴车要走七天,再后来“提了速”,路填成石子混沙,毛驴车换拖拉机,车马劳顿,走走歇歇,时间缩短了一半,到城里也要三天。落户草湖的各族群众,不能仅依靠耗时劳力的运输带来补给,在自然中探寻,以此果腹,是人类天生的智慧。
塔里木乡像是个隔绝开的小桃园,春有山花开遍地,夏有芦苇塘野鱼,秋有胡杨林满野,冬有落雪掩塔兔,北临世界上最长的流动沙漠公路,这条公路贯穿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接天山雪融的阿克苏河、喀喇昆仑山的叶儿羌河及和田河,三河汇流形成的中国最大内陆河塔里木河。
同事李姐,原籍陕西,生于草湖,父辈招工入疆,而后落户塔里木乡,是当时羊场里唯一的医生,那时塔里木乡还称草湖,少数民族群众多以畜牧业为主,鲜少农耕。随着这一批知青的流入,垦荒种地,饮食结构逐渐丰富,从较为单一的少数民族餐食,烤肉、汤面、曼塔(维吾尔语意为包子),开始有了油条豆浆、稀粥小菜,也为这自给自足的桃园带来混合与融入。物资不够充裕的时期,人食五谷杂粮,难免身体不适,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接纳一位汉族医生,从初期怀疑试探,到认可和收获,现代西医与传统维医疗法取长补短,逐渐凸显出优势,而病愈后的百姓表达感谢的方式之一就是饮食补给。
儿时的李姐常会发现门缝塞进来的布包,里面包着新鲜的土鸡蛋,再就是放学回家发现门口挂着一只野兔,或者是活蹦乱跳的野鱼。
对于草湖的美味记忆,就是童年里各种野味的混合。维吾尔族群众是不吃兔肉的,长久相处,知道汉族群众善于处理这一野味:野兔宰杀简单清洗后,放上蒜头、辣子,快火爆炒,闻着味道进来的同乡邻里相互打着招呼,齐坐畅饮,埋头在热气腾腾的锅边灶沿,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野味虏获了贪恋肉欲的味蕾。
有河,有山,有树,千百年来不断进化出塔里木特有的野味,这里说的野兔其实就是塔兔,只分布塔里木盆地,又称南疆兔、莎车兔,体型较小,体重四五斤,色浅毛短,头背呈沙褐色,体侧毛微黄,腹部白色;耳长尾短,一双大耳朵几乎占据身长的四分之一,在胡杨林及红柳丛生的灌木丛沙包包里筑窝打洞,以芦苇及沙漠植物为主要食物,吃食天然,奔跑跳跃,活动量大,肉质紧实。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是顺应自然的中国式生存之道,或许是无意发觉,又或者是有意探求,总之自然中美味被发现,续而被认可。草湖天然的地域屏障,戈壁滩上、胡杨根下、泥窝子边边……撒欢成群的野兔并不怕人,它们各自快活,与同样居住于此的草湖人相融相生,但终究架不住口口相传“好吃”二字,人类在短时间内使之变成大众化食物,原本限于调剂补给的食材,完全供应不了日积月累的消耗。
塔兔一年繁殖两三窝,从2月开始至7月期间雌雄兔交配产子,一窝2~5仔,原有数据记载,塔里木盆地塔兔总数量有二十万只之多。如此庞大的数量和繁殖力极高的物种,随着栖息地丧失、沙漠化侵害以及捕猎,如今已濒临灭绝。早在八十年代,塔兔就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时我在草湖时就已难觅踪迹,老草湖人念叨的是昔日味蕾上的畅快满足和赞叹。
类似于塔兔之类的野味,新疆很多,伊犁河沿岸的野猪、赛里木湖边的野鸭子、戈壁滩上的黄羊、塔里木盆地的野鸡、野地里的刺猬、阿勒泰的狗鱼,还有很多叫不上名的物种,它们曾经充盈一代代新疆人的味觉记忆,现在要么频临灭绝,要么数量速减,早都是国家一级、二级、三级保护动物。
还有山间林中各种各样的菌类。
没有什么是可以脱离自然独立而生的。餐单上的丰富,舌尖上的满足,是时代的进步,亦是社会的发展,单一到繁冗的过程里也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不是一味地向前走,而需要回身寻找,尊重本源、尊重环境,莫让某一种味道成为子孙的听闻,让他们能看到、能尝到那自然的味道,才是我们最大的智慧。
作者简介:江炜,新疆公安,一级警司,爱写字,爱美食、爱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