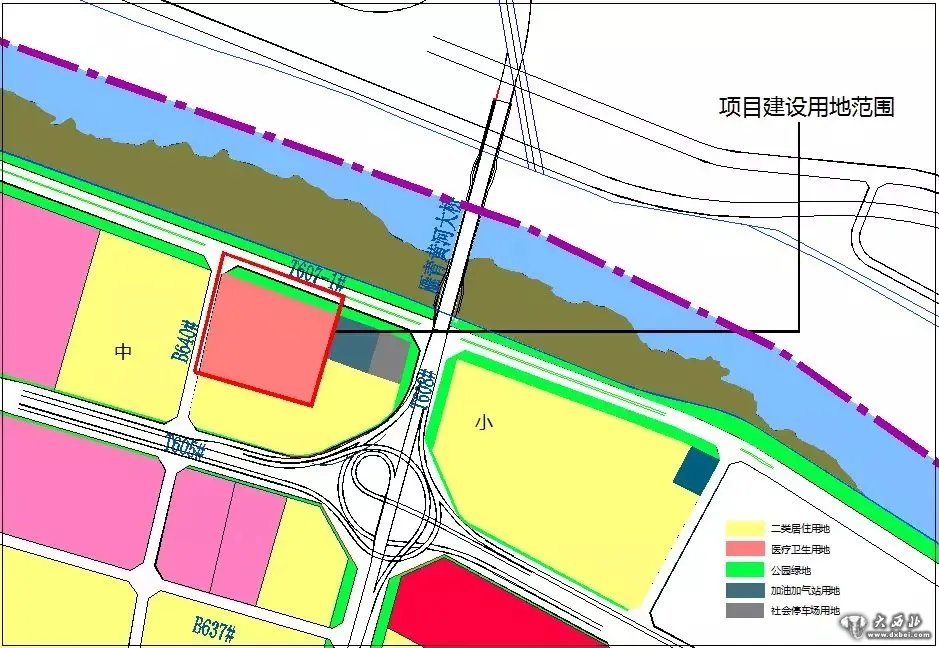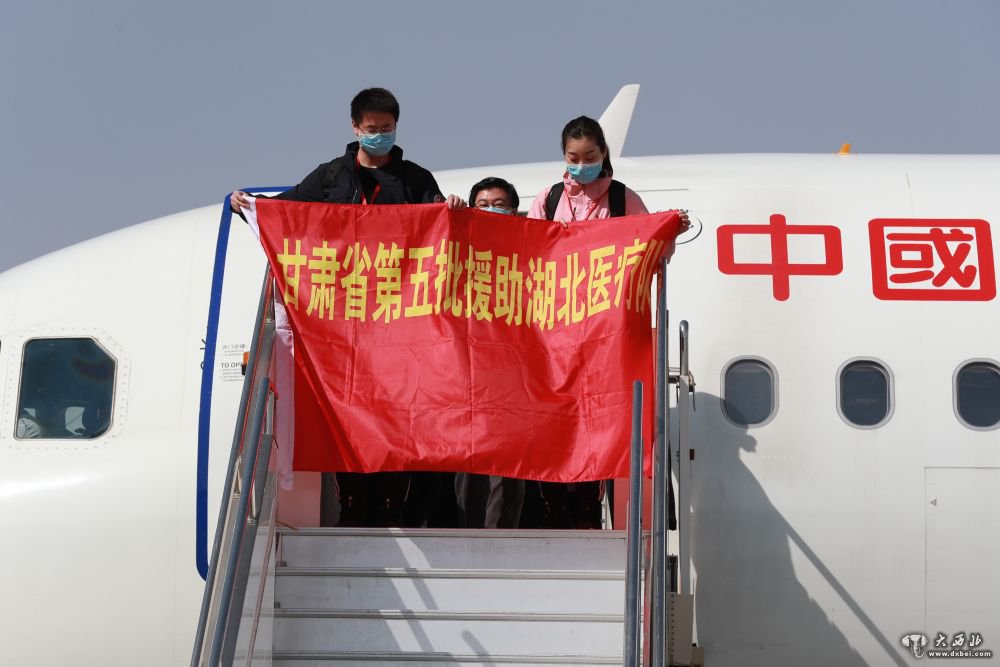很多记忆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堆积着,它们愈加显得厚重与有质感。当你轻轻地走过它的身边,轻轻地将自己身上的现代气息施加在它的周围,那些许留在历史中难得的故事被你带走了。慢慢地,慢慢地这些故事就成了一个安静的谜。而与这些故事同在的建筑,却依旧在寒风中傲立。虽然现代工厂中的油漆早已覆盖住了百年以前的斑驳,但当一双双手抚摸那些年老的木质支柱时,也许就在那一刹那的时空交错中,许许多多的叙述只是一阵风,一粒雪花。
不期而遇
我始终认为,人与一座建筑的故事也是有缘分的。当在这条细小而安静的巷子里看见这座孤独的建筑,我慢慢地开始用心去体会,用内心久远的纯粹去读懂它。
“道生无极成始成终成万物,德尊太极至高至大至文昌”,漫步走来无意之间抬头看见一副不知出于何方高人之手的对联,似乎这短短的22个字将人生说完了,品尽了。轻身而入,跨过高过小腿的门槛,站在院内。清静的院子里,没有他人,也没有别的声音。一栋与周围建筑相比显得矮小许多的建筑在正中间矗立着。
在这条名为春风的巷子里,寒风正从两边吹来,屋檐和枯树上落满了积雪,也许百年以前的日子就是这样的。站在院子里,没有人和我交谈,也没有人来询问我。在已经有些残损的石板上,除了历史的痕迹似乎也就剩下我走动的声音了。在这个不大的院子里,抬头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这些红色的柱子,如今的柱子早已不是百年以前的了,窗户和红色的大门都让人有一种回归的感觉。从屋下向上看,屋檐上的彩绘异常漂亮,而那翘起的房檐给人轻盈的美感。整个屋子略显空旷,中央的莲花上坐立着“文昌帝君”,让人感觉很威严,仿佛他能够看清站在面前的人心中那些灰色的、邪恶的念头。塑像很精致,让人不免要多看几眼。
走出文昌阁,不期而遇地见到一位老人。老人名叫李庆国,今年63岁,在春风巷已经住了有40多年了,他记忆中的春风巷有着另外一种阐释。
李庆国大爷说自己已经老了,不会像文昌阁这样焕发新春了。他记得很早的时候这里虽破旧,来这里上香的人却很多。也许对于李庆国大爷来说,生活总是在遗忘与寻找中前进着。李庆国说:“以前二三十岁的时候觉得每天风尘仆仆,时间过得很快,可是当慢下来时,年龄就已经大了,突然发现身边的许多物件已经变了样子,想再寻找都找不出回了。”
是啊,对于李庆国来说,现在的日子就是沿着这栋屋子的外墙出去然后再回家。每天早晨和黄昏时分,李庆国说自己都喜欢来这里瞅瞅,找一找关于自己年轻时候的记忆,也许不知道哪天会记起以前文昌阁的样子来呢。
文人福地
李庆国大爷记忆中文昌阁庙火兴盛之时的样子,记者已经看不见了,但是从一些资料和专家那里可以知道一些关于文昌阁大致的概括。
根据乌鲁木齐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介绍,史料记载 “文昌”本是天宫名,古代星相家解释为大贵的吉星,道教将其尊为主宰功名利禄之神,又叫“文星”。因文昌星和梓潼帝君同被道教尊为主管功名利禄之神,所以,二神逐渐合而为一。
清代嘉庆六年,礼部将祀文昌编入礼典,天下府县处处建文昌宫,每年农历二月初三祭奠。1765年老乌鲁木齐建城,至1884年新疆建省以后,这段早期历史是新疆发展文化和教育的重要阶段。当时,在兴办教育、恢复和新建义学的同时,新疆省政府还在迪化建文庙、文昌宫等场所,供文人、学子祭拜。1925年前后文庙迁到此处。到盛世才统治时期,这里逐渐荒废,解放后成为军区家属院。
文昌阁原先方位坐东朝西,2003年规划维修时,因场地制约,将文昌阁改为坐北朝南。如今的文昌阁几经修建,仍然保持着中国古代庙宇的建筑风格,檐外挑枋、上雕龙兽、栩栩如生,殿堂内文昌帝君充满智慧的神态,吸引着文人墨客来这里祭拜,许多人在这里挥毫泼墨,思文吟诗。
在与乌鲁木齐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许淑云的交谈中,记者更是知道了一些非常让人欣喜的秘密。原来看似不起眼的文昌阁,却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章回体小说《老残游记》(续集)和散文《白杨礼赞》等都诞生于文昌阁,如此一说那文昌阁真的是文人的福地了。
1908年的春天,刘鹗被当时的清政府头子袁世凯定为 “通洋”,落难到老乌鲁木齐,身无分文,走投无路,与此同时,他创作的小说《老残游记》,正风靡北京城。刘鹗被当时的新疆布政使王树楠安排在文昌阁居住,乌鲁木齐胜似江南的景色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他每天苦苦创作,在文昌阁写出了《老残游记》(续集)。
民国年间,著名的文学家茅盾和《抗日报》记者杜重远,先后来到新疆采风,让后人好奇的是,他们均在乌鲁木齐市文昌阁居住过,而且在这个祭奠文昌帝君的楼阁内写出了著名文章《白杨礼赞》和《新疆通讯》。
过去的都随风远去,无法知道的和难以清楚的成了传说。李庆国大爷还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过去。而文昌阁不仅是变化了位置,它百年来的故事和不为人知的历史都成了角落里的灰尘,希望这样一篇简短的文章能成为一根火柴,让喜欢的人去挖掘,去探寻文昌阁的过去和记忆。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