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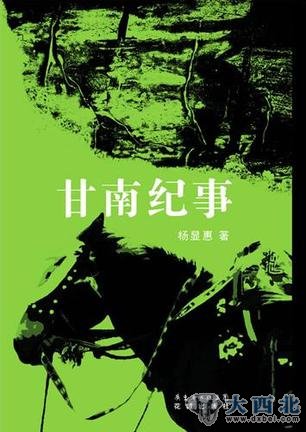
杨显惠
1946年生于兰州,现居天津。曾在安西县小宛农场参加上山下乡。1971年入读甘肃师范大学数学系,1988年入天津作家协会专职写作至今。曾出版《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等重要作品。
杨显惠的《甘南纪事》共16万字,比之前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薄了不少。全书用了十二个故事讲述了甘南的风土人情故事,是2009年杨显惠在《上海文学》杂志上连载了一年的同名作品。《甘南纪事》号称是“命运三部曲”最后一部,实际上,这个名号根本不是杨显惠和该书编辑林贤治的意思,杨显惠告诉记者:“《甘南纪事》和前两部作品没有任何关系”。他以为“三部曲”的说法来自文学评论界,而林贤治说,“命运三部曲”是某网上书店宣传该书时的口号。
《甘南纪事》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从2006年春天开始,连续三年,杨显惠都借道兰州进到甘南藏区,住进藏民的牛毛帐房和沓板房。2010年的冬天还没过,杨显惠去做冠心病复查,心脏里本来有五个支架,这一复查又做了手术加了三个,在上海文学连载一年的《甘南纪事》就此停下来了。手术后,他一直安心养病,放弃了继续写作甘南的计划。今年六月底,他又去了甘南,这一去就是三个月。
12月中旬,《南方周末》“中国梦”活动邀请杨显惠到广州,论坛活动中,他做了一场名为《先让农民崛起》的演讲,和他一起讲演的还有秦晖、袁隆平、易中天等人。在广州,杨显惠也见了林贤治。他的“三部曲”都是在花城出版社出的,之前仅和林贤治见过一面。林贤治并不避讳对《甘南纪事》的不满意,他认为作者应该有把握写作题材的能力,前两本书,杨显惠找到了很好的题材,而这本甘南纪事,杨显惠有些被题材带着走。“藏区在这个时代的变化他并没有把握得很好”,林贤治说。
杨显惠深知林贤治是一个“思想型的作家”:“这本书肯定令他不是很满意。”杨显惠坦言《甘南纪事》“没什么价值”,“一个是薄,轻飘飘的;二是没有很沉重的感觉,这是心理的感觉。写完前面的两部作品之后,我想换一换,换一个轻松的题材,当然在换轻松题材的时候,我也想弄清楚藏民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我并不想挖他们沉甸甸的历史,我就想看看他们现在是怎么生活的,这就是这本书。”
想写写改革开放后甘南的现实
南方都市报:人们称《甘南纪事》为“命运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你怎么评价它?
杨显惠:我自己并没有将它们定为三部曲。我没有这样想,也不赞同。但我也没反对过。
南都:那它跟前两部有渊源吗?
杨显惠:没有,基本没有。前面两本是我选择比较重大的题材去写,表述我们国家从1949年以来历史上两个重大事件。《甘南纪事》我没有进一步想法,就是想写一写改革开放以后甘南那个地方的现实,人们是怎么生活的。我自己没有给自己选择一个什么主题。我就是想写他们的现实生活。
南都:认识藏民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如何与他们打交道?
杨显惠:我认识藏民中的一个人,他跟其他人很好,他介绍我到其他人家里,在别人的家里可能又认识了其他的人,那我就这样不断地周转。最初认识的几户家庭,我每次到甘南都会去。我每一次去都是十天半个月,最多二十天的时间,然后在兰州过上一段时间,再进去一次。每次和他们认真谈话,我有一个录音机,随便聊天的时候,录下来,聊完了再写在笔记本上。这些故事都是观察得来的,不是我这次去了就有哪些故事在等着我,而是日积月累的过程。
南都:关于你的作品,包括前面那两部,读者总有一个疑问:书里写的是真实的事还是虚构的?真实和虚拟的边界在哪里?
杨显惠:我住在一个牧民家里,你跟他熟悉了,他就告诉你,他的姐姐是怎么谈对象的,怎么跟丈夫跑了的,父母是如何反对的,这实际上,一个故事就给你讲完整了,有些他给你讲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很震撼人,那么我再编一个故事,围绕这个细节为核心。有些故事他的框架有了,但是它的细节不精彩,那么我就运用别的细节给它补充完整。可以说,每个故事里面都有一个真实的人的影子,有某个真实故事的框架,或是某个真实的细节,“真实”是多种多样的。
南都:从文中举例来说,哪几个是真实细节,哪几个是真实的故事?
杨显惠:比如,《白玛》这个就是真实的细节,女的已经出嫁了,但是她还有情人,她跟情人会面,她的丈夫知道了,就拿刀子把情敌的脸上划了一刀。这个印记让你走到哪别人都知道,你是一个坏人。这是过去藏民的一个传统,我就觉得这个细节非常好。
《给奶奶的礼物》就是细节衍生出来的,我听他们说,一个牧民老头,到现在他夏天穿毛磨光了的皮袄,冬天穿长毛的皮袄、裤子,一个布条在他身上都看不到,这就是传统生活在他身上留下很深的印记。
生活在最美的大自然下的一个民族
南都:接触藏民,对你来说感受最深的东西是什么?
杨显惠: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们是生活在最美的大自然下的一个民族。我感觉这个民族很温和、对人很好,非常吃苦耐劳,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非常美丽,但生活很艰苦。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生活的这么一个民族,他们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宗教、文化、生活习惯,很多跟汉族人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吸引住了我,我就连续几次去了。
南都:可不可以说,一个民族拥有宗教,更有敬畏感?
杨显惠:关于他们的文化、宗教,其实我也了解得也不是很深,所以你看我写了的这十多篇里面我基本上没提到宗教。他们全民信教,不像基督教,孩子生下来后要受洗,他们没有这种意识,没有形式上的遵循,他们就生活在全民信教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了都是佛教徒。所以我觉得佛教的信仰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东西。
南都:但是我看你在故事里面也写到,比如他们为了牛鼻子绳这样的小事会拔刀相向,你说他们是一个很平和的民族,但这样激烈的东西也会有是吧?
杨显惠:对,实际上这样的东西也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种,我觉得是这种环境、生活方式造成了他们思维上的这种放肆。他们的思维、价值观和我们有不同的定义。
南都:这种思维就是指他们有时候都会用武力去解决问题?
杨显惠:不能说这个民族是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他们有很多都是遵行他们的心,他们的生活本身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身上带着刀子,并不是为打架、武力征服。藏民过去是以肉食为主,肉咬不动怎么办?他们拿刀子一块块在骨头上削着吃。刀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生活用品。现在吃面粉、大米吃多了,刀的用途就少了,带刀的人就少了。另外,那里的男人们都是骑马的。要是马惊了,人被马镫套住了,叫套镫。这时候,拔出刀子来把马镫的皮条绳割断就能活命,如果不带这个刀子,可能马就把他拖死了,所以这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工具。
可是遇到他发怒的时候,刀子就成为他的武器。所以我觉得是他们的生活条件本身造成这样一种表象,好像他们爱动武。实际上也不是。如果我们汉族人每个人在腰里也带一把刀子的话,可能用刀子解决问题的次数比他们还要多。
南都:他们现在的生活有没有受外面世界的影响?
杨显惠: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过去的藏民生活中吃饭,主要是吃糌粑,就是青稞炒面拌上酥油茶。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吃花卷、馒头、面条、米饭了,这些东西已经在他们生活里面占到主要成分。这个是生活中很细微的变化。另外比如说藏民1958年以前穿的衣服,没一个布条,全部是皮的,靴子是牛皮的,衣服是羊皮的。现在他们的穿着以布为主。所以说他们的生活都在不断变化。
南都:那么他们在精神上、思想上,也有这种变化吗?
杨显惠:这个变化我觉得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过去藏民没有学校,他们的学校就是寺院。每个家庭除了老大要继承家业,要放羊放牛,继承家业,老二、老三都要送进寺院里当和尚,八九岁就送到寺院里面,一直到老。而现在当和尚的人越来越少了,寺院的和尚的来源已经不足了。现在很多家庭把孩子送到学校里边去上小学、中学、大学,能够上大学是他们比较高的理想。他们现在也知道孩子出外打工,人家都要高中生,没有个高中毕业的文凭,就只能干什么盖房子、挖地基、修公路这些体力活。他们现在认识到学文化的重要性。这个改变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进步。
对一个地方,要四五年才真正熟悉
杨显惠:这个也说不上什么感情,我觉得走到哪个地方都行,我这一辈子19岁离开兰州以后再就没回到过兰州,回去也是住上几天、一两个月就离开了。可是我觉得我的写作遵循一个原则———写一个地方我就要熟悉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弄熟了,写作才能深入,不流于表面化,想到要让它深入一些,所以我始终在写甘肃。
南都:要写自己独到的东西?
杨显惠:对一方水土、一个题材的熟悉我觉得是得几年时间的。比如说我自己这十二三年来,写《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然后写《甘南纪事》,每一本书写出来得四五年。当然你说我可以在城市里,写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写医疗问题,我去医院熟悉一下、做些调查,这样几个月就可以熟悉,但那仅仅是很窄的面上的调查。生活的质感在文学里面要表达出来,我觉得没四五年时间不够。因为文学创作,我认为是一个理性的思考,你应该把这个地方的题材抽象出一个哲理的东西来。但是同时,你在写作当中,细节、故事必须有很多质感、形象化的东西,你不能把它写成一个哲学著作,不能用数学的思维去思考它,你必须拿形象化的东西来描写,这就需要你对生活有足够的感受。所以写一本书我觉得得几年才够。
南都:《甘南纪事》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下一步的写作方向和思路是什么?
杨显惠:还是按照这个方式来写,把它写完吧,至于以后出续集还是修订本,我还没有什么想法。后面的稿件还没有开始动笔,这个作品算得上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他们现在的生活很多方面我就没有谈到,比如,藏民的宗教信仰。他们是全民信教,当然不一定是佛教,也有一部分是信仰本教、道教的,这方面都要写。再比如,藏族的年轻人对老年人是很尊敬的,虽然社会发展到今天,但是老年人说话,年轻人是要听的。我们年轻人的独立意识强,老年人的话可以不听,或是不赡养老人,这在藏民里面是没有的。我举这两个例子就是要说明,藏民的方方面面我还没有写全。下面我还要写故事,也是十几个左右,和现在的篇幅差不多。
南都:这部书显得比较薄,也还没有写完,为什么急着出版?
杨显惠:甘南纪事在上海文学上发了一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向《上海文学》提出,要把今年在杂志上发表连载作品的作者编一套上海文学丛书,有刘心武、王蒙等人,算上我一共是五个作者。在上海那边提出出版之前,花城就提出我把这个作品写完了,他们出书。上海稿子已经编了,没出成。这边就说,没出成更好,我们出不就行了么。这本书出来了。
我对林贤治说,老林啊,你心里肯定是不满意的。林贤治说:这本书拿出去和别人比,还是一本不差的书;可是比他心里预期的,不够。我这本书没啥思想,在这个层面上,林贤治是不满意的,他还是希望我写的更加厚重一些、深刻一些。
南都:贾平凹也写过定西。在之前你看过关于甘南的其他作品么?是否有过参考?
杨显惠:关于甘南的不多,关于藏民的是有一些。四川的扎西达娃、阿来,云南的范稳,都是写藏民的,他们的写作都带有先锋写作、现代派的写作手法,而我的是一个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阿来的《尘埃落定》写了奴隶制度必然解体、新的社会制度必然建立起来,它表现了这么宏大的主题,获得茅盾文学奖。范稳的《水乳大地》则带有魔幻主义的味道,写基督教和佛教是怎么碰撞的。扎西达娃写西藏的新生活,他们对藏民的生活肯定比我了解,我是在藏区打了个游击,这跟人家没法比,没法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比较。
如果说我的写作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一个外来汉怎么看藏民的生活。谈不到历史,也谈不到未来,就是一个片段、一个横截面,看到他们现在怎么生活。我知道我写不深。我是不想沉浸在之前沉痛的历史中。
南都:之后你有什么创作想法?
杨显惠:下一部,我想写我的知青生活。1965年我高中毕业,大学都没有考,满腔的热血要建设新农村,纯粹是一个热血青年进入社会。我从甘肃的兰州跑到最西边的敦煌和安溪交界的地方,当农工、售货员、农垦中学教员,这十六年的经历我都要写出来。写这个我就用不着到处跑了,只需要我坐在家里。那里面肯定要带一些对社会的思考,对我人生的思考和总结,也可能从个人的生活折射出社会的变化,希望做到这一点吧。
采写:南都见习记者赵大伟
摄影:熊靖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