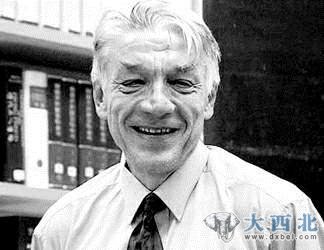
顾彬
在1985年以前,民主德国不允许他们的人民关心中国,看有关中国的消息。“在东德基本不能学汉语,他们只允许几个人学现代汉语。”顾彬说。他生活在联邦德国,1966年他的学术志向由神学转为汉学,因为神学里看不到人,他需要跟人在一起。
顾彬熟悉远在东方的中国,也熟悉邻邦民主德国。他认为民主德国害怕中国,尤其怕1979年以后的中国:“他们采取的是禁锢的政策,就像他们修建的柏林墙。”
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开始修建的时候,顾彬15岁,在故乡敕勒,德国北方一个古老的小镇:“我跟祖母听到修建柏林墙,非常难过。”
顾彬真正看到柏林墙是在1977年搬到柏林以后。他住在离柏林墙很近的一幢房子里,属于当时的一个工厂区,非常破败,当时没有人想住在那里。“但是知识分子、文学家、作家、学生很喜欢那个地方。”顾彬回忆道。
2009年11月4日上午,在柏林墙倒塌20年之际,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清华园专访前来出席国际汉学大会的顾彬。
满头银发、瘦削、神情严肃的顾彬在旅馆的房间里冲好咖啡,思绪回到他记忆中的柏林墙。
那时他们最怕中国
南方周末:据说当年柏林墙有70万枚地雷,6万支自动扫射机关枪,还有1100只训练有素的狼狗,东德领导人也有“越墙者射杀”的命令?
顾彬:这个数目我不太熟悉,但是报道肯定都是有道理的。1985年我住在柏林,差不多每天都能看到柏林墙,柏林墙前后都是空地,东柏林到处都会有炸弹。有时候我去东柏林,他们的检查非常严格,因为我是汉学家。那时他们最怕中国,最怕1979年以后的中国会影响到东德。
在原来的西柏林中国非常红,每天都有报道。有一次,可能是1980年代初,我去东柏林的时候,身上带着电台的海报,海报上是预告明天要报道“中国‘文革’”专题。海关发现了海报,问我为什么把这个海报带到民主德国去,他把海报收走了,他们怕东德人会听这个报道。
南方周末:民主德国为什么会害怕跟他们一样走社会主义路线的中国?
顾彬:中国从1979年开始不是走向改革的路吗?他们怕东德人发现他们的社会主义有问题,然后从中国来看他们走的社会主义。无论是“文革”的中国,还是1979年以后的中国,他们都怕。
南方周末:德国的统一被看成是冷战的结束,整个东欧变革的象征。
顾彬:是。但这么多年以后,我认为东欧的变革没有中国成功。因为他们没有经济基础,也缺少民主精神,搞得好的还是原来的民主德国,现在虽然还落后一些,但是跟1989年比起来,发展也不错了。原来他们城市完全被破坏了,民主德国没钱修,现在好多原来难看的城市都非常漂亮。但是现在德国东部的人还是觉得非常不公平。因为西柏林无论经济还是城市面貌都比东部好,觉得发展得慢。
我觉得变化慢一些很好,中国的变化就是太快了,中国人自己也跟不上这个发展速度,原来特别好的代表城市面貌的东西也都拆掉了。
政治家们觉得“我们完蛋了”
南方周末: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你看到的德国民众是什么样的反应?
顾彬:都高兴死了。我们很想德国作为一个国家统一起来。另外他们的社会主义和政治体系也是有问题的。举个例子,我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想在柏林开一个现代汉语大会,因为当时的民主德国出了一些非常好的中国现代汉语课本,尤其是1950年代的。我想请他们来开会,他们怎么回答呢?你们是帝国主义,我们不来。他们总是批评当时西德的人,是美帝国的走狗,不管是老百姓还是政治家们,都这样批评。其实那时候西德知识分子中有很多左派,他们也对美国的经济模式持批判态度,也反对美国,也反对越战。
南方周末: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顾彬:我在波恩大学教书,我们都在关心中国,1989年的中国。
从1980年代初东德就已经投降了,因为东德没有选择中国之类的路——如果东德跟中国一样,从1979年走上改革之路的话,可能它现在还在。东德的消失有两个原因:第一,没有进行经济改革;第二,它还在控制着人民,控制太厉害。
1980年代中国人可以到国外去,虽然很麻烦。但东德根本不允许国民到西方国家旅游。还有就是他们没有什么物质基础。从1980年代初开始,当时西德政府给东德很多很多的钱,因为他们差不多破产了。当时西德政府怕东德会发生什么动乱,怕苏联的军队跟进布拉格或匈牙利一样来东德,镇压那里会发生的什么起义之类的活动,所以当时西德每年给东德很多很多的钱,但是没有人公开说这些。1989年之后,埃利希·昂纳克下台后,接替他工作的那个人很清楚,没有办法独立下去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那时候没有派什么军队阻止人们逃亡柏林,没有阻止当时的东柏林的人把柏林墙拆除,政治家自己觉得“我们完蛋了”。
跟东德的社会主义不一样
南方周末:1989年前的东欧,整个社会形态都处于被禁锢的状态,知识分子的思想有没有自由?
顾彬:对,但这些作家可以在西方发表他们的作品,所以当时无论是哪个东欧国家都有好的文学作品,即使是在被禁锢的时候。
南方周末:在封闭和禁锢的时代,东德的知识分子的状况如何?
顾彬:东德作家分三类:一批跟当时的政府合作过,做顾问,这是德国的一个固定名词——“顾问”,就是你老要给他们写报告,某个人在想什么、做什么,不少作家跟警察机构合作过;另一批不一定这样做过,但他们自己觉得民主德国是不错的;第三部分作家,对民主德国持批评的态度,但是他们不否定社会主义,只是觉得他们的社会主义有一定的问题,应该改,所以通过作品表达社会主义改革的希望,这些书他们没法在东德发表,就在西德发表。发表以后,他们就要面临一个选择,离开东德去西德。很多人要求留下来。
有个非常有名的歌手、诗人,叫毕尔曼(WolfBiermann),他希望民主德国改革,所以经常用中国因素来表示他的期望。比方用长城之类的象征。一次他去西德朗诵诗歌,民主德国也派特务去,让他们报告他的情况,最后决定不允许他回来。大部分当时民主德国的作家,也包括艺术家,相信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相信的那个社会主义跟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可能不一样。
南方周末:西德的作家状况呢?
顾彬:西德的作家有不少主张中国式社会主义,大部分作家、艺术家都是苏联式的左派,受“文革”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从今天来看,他们当时对中国的了解很有限,所以到了1980年代开始,慢慢了解“文革”。不少受到“文革”影响的作家们,后来公开地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原来西德的政府跟西德的作家关系非常不好,互相骂,到了1989年以后情况好一些。虽然作家经常和政府对立,但他们还是能够发表作品,能在任何公开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
最应该思考对人的解放
南方周末:德国统一也一直有反对的声音,君特·格拉斯曾批评德国统一是违宪行为。
顾彬:格拉斯敢说,但我觉得他的立场有一点问题,他也说过我们西德占领了原来的东德,我觉得这是胡说八道。但是他有代表性,有不少人觉得民主德国应该是独立的,他们应该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柏林墙倒塌,为什么?人不能骗自己。包括知识分子在内,都要面对具体的问题,1989年之后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对人的解放。柏林墙的倒塌,在我看是对人的一种解放。
南方周末:德国经历了意识形态的变革,这样的变革对国家的影响大吗?
顾彬:非常重要,意识形态会帮助一个国家发展,所以中国需要思想勇敢的人。不要怕什么,如果有什么错的看法,可以改。
南方周末:意识形态的禁锢与封闭只会导致社会的倒退,甚至崩溃。
顾彬:是,肯定是。有人说是全球化时代,我说是合作时代。
比如,不少人认为德国才实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理想,因为我们是福利国家,人们没有钱也能过比较好的日子,也有人说,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对社会主义如何定义,还是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在德国还是影响很大,他们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比较具体的,就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给老百姓带来好处?”所以无论是基督民主党,还是自由党,他们都考虑人们怎么能够更好地过日子,所以社会主义的思想对德国每个政党都有影响。但是,最重要的是,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际上,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提高人民的生活。
南方周末:对于中国的作家,你有什么建议可以分享?
顾彬:有些当代作家,他们把文学看成是玩具,但是文学是非常严肃的东西。另外作家应该勇敢,应该敢于公开提出社会的问题。德国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人的精神危机越来越严重,现在人们不是去找什么牧师、什么神父解决精神上的问题,他们是去找哲学家,找作家。中国的作家不像西方作家对社会、对公共事务那么关心,那么深地介入,西方作家经常会直接出来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最近作家余华在德国发表演讲,谈到了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这样做非常勇敢。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作家要向他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