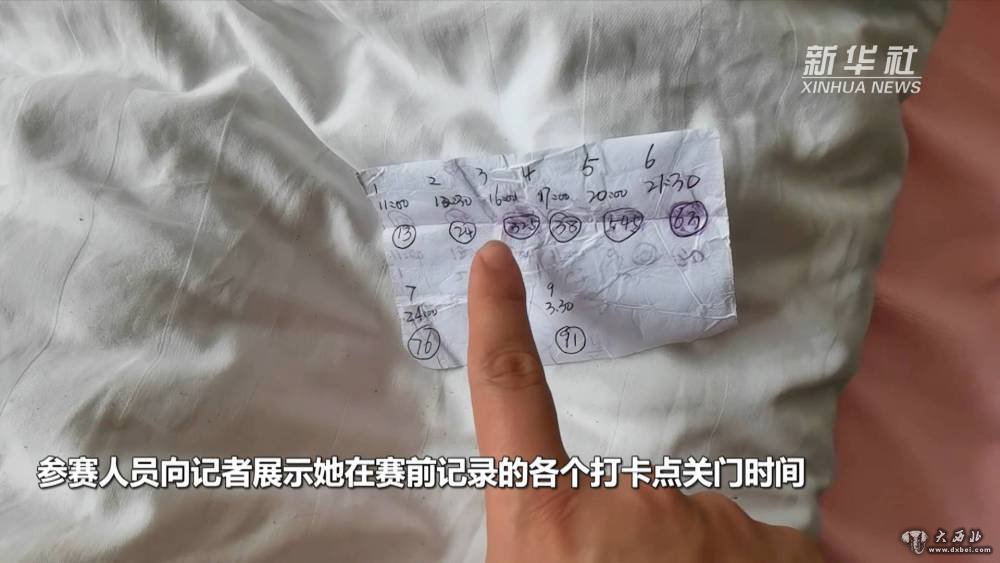诗曰:
黄河东流去,岸边向北行。
蜿蜒六七里,山青野花红。
山村名水源,炊烟袅袅升。
我念桑梓深,日月牵乡情。
归来结草舍,苍桑天命身。
筑屋在道边,夏听蛙鸣声。
朝迎红日升,夜沐月光明。
薄地两三亩,地贫人辛勤。
风雨春秋忙,种得瓜甜香。
盘中菜蔬鲜,皆自田中产。
味美纯天然,少有农药染。乡邻皆亲人,老幼尊长严。
闲时农家院,也听诗酒欢。
门外车马稀,小犬捕雀闲。
犬吠客进门,来往皆乡邻。
语虽有不雅,言来必赤诚。
山上草色青,野鸡唱其中。
晚霞映山廓,飞鸟归黄昏。
休言山野偏,我自心向远。
此间得真趣,于君话闲言。
摘自《闲吟集》
这是一个即将消失的村庄。我只想在她蝶变之时,记下我所知道的她曾经的过去岁月的只言片语,以做抛砖引玉的引子。

很久很久了,总有一种想为我生于斯长于斯,我的祖祖辈辈生活生存的山沟沟里的村庄,这个名叫“水源"的地方说点什么。但每每欲说,又总是在心中的很多纠结中讷言。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自己近乎文盲的无能和对这片土地所承载的历史的无知,对此自己常有深深的汗颜之感!
省会金城沿黄河东行,站在通车不久的宽阔平坦的盐什公路的河岸,从此处向西望去,浩浩荡荡的黄河,奔腾起浪花,激荡出旋涡,咆哮轰响于此处折了个弯向东面的桑园峡流去。抬头望,一桥飞架两山的柳忠高速路上,车辆从头顶上飞驰而过,与它下面的大河一样不舍昼夜。桥下两山之间有沟,旧称小沙沟。沟口的高杆上端,有块牌子上写着“水源甜瓜基地”的字样。一条简陋的水泥路与盐什公路相接,入沟前行,地势渐高,路崎曲蜿蜒,路面多有破损。左侧是裸露的红沙岩的崖壁及上面高耸的山峁,右侧的沟底有咸涩的溪水顺势下流而去。进沟一两公里之内,沟两边的山上,多有丹霞地貌的红沙岩壁或高或低的呈现在你的视野中。曾经自然形成的似兽非兽,似鸟非鸟,似麦垛,似屋宇的天然的红沙岩景观,在当今满世界的开发开挖,征用抢建中几乎都没有了踪影!最有名的处于似有一线天之险,历史常有土匪出没的“狼舌头"景观也在这两年被附近郊区的人们,因听说要扩修公路,抢拓土地要补偿而掩埋了。过了此险要之地,再拐两个弯,山势顿开,看到包兰铁路,兰渝铁路分于两边的山侧,穿山跨沟,时有长龙般来往的客货列车快速驶过。再往前行数里路,便可看见散落在高坪低台上的农家院落,大多是朝阳而居。

西北干旱,地瘠民贫,古来有名。大多以“水"字之意为名的地方,无不因缺水为昐反其意而用之。"水源"村之名概没能外。这一点从现在水源的五个自然村庄的名称就可见端倪。一社卲家塘,二社潮泥沟,三社甘井沟,四社上水头(水源),五社下水头(马家铺子),所有的名称无不与水有关,表达着对水的心声。从前除上下水头两个村庄的河沟里有地下溢出的清清溪流可用外,其余村庄生活用水,都是在沟谷里挖数米深的井,肩挑手提回家做饭洗衣。水虽味咸,但可养人。祖先们便在此结束了背井离乡,开始了生存繁衍,生生不息到了今天。
上水头村庄河沟里的水流过下水头村庄时,夲就咸涩的水就更苦咸的无法食用了。上下水头村庄的河沟里,从前各有一眼清泉溢出,人们便从泉眼处接水以用。四季不断的泉流,便汩汩于低洼处,汇成无数个水塘,也常有波光粼粼之趣,只是面积都是几到几十平米大小不等,到夏天水里蛙声一片,日夜呱噪时,老人们便说天要下雨了,确也十不离八九,两三天内必有雨降,只是雨大雨小由老天爷掌控。冬天因结冰水流不畅,水越积越多,冰面就越冻越厚,面积就越大,河沟窄的地方冰就布满了沟,行人,车辆,骡马就都从冰面行过,冰面下的水却还继续着它向前的行程。滑冰戏耍后的娃娃们,回家时便刨下晶莹剔透的冰块背回家烧水煮茶。说来也怪,冰化的水竟少了原先的咸味。便有将冰块或冰化的水存放到天热,专门招待家中来客。也有从稍高于沟底的地方淘井而用,以保证人畜分用,干净卫生。但水依然是咸的,却有个好处,煮肉,做饭是无需放盐的。那沟里流淌的溪水便是驴,马,羊与天上的飞鸟,夜晚的走兽汲水的乐园,也是天热时人们浣衣洗物的去处。水越往下流越苦咸,自然是无法浇田润地,十年九旱的土地只能靠老天雨水的滋润了。那沟底的水却在阳光里闪着欢快一直流进前方的黄河中去了。好在聪明的祖先们发现了铺压沙田,保墒保产伟大实用的生产方法。但那又是一种不仅仅是勤劳辛苦所能完成的事情。因为要开山洞取沙,或挖地深十几米的沙井,用简陋的工具将沙石运出,用人背,或独轮车,架子车,或牲口驼运到半山的,坪台的田里。地下的沙井,山上的沙窰塌方,或伤或亡,其中有多少的艰难和生命的负出,难以想象……,多少年多少代,这里的人们就这样在艰辛与苦难中,在消失生命的代价中,经历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爱恨情仇!

土地虽然贫瘠,人却生来勤劳。就有了瓜甜麦香的日子。盛夏时节,水源村的各种瓜品成熟季节,满沟都是清香的瓜甜之味。山间的路上,白天黑夜便多了摘瓜运瓜上市出售的人流,车流。那名闻在耳的白兰瓜,成熟后先绿后白,切开是莹莹如玉色,流淌出蜜一样的汁液,忍不住咬一口厚厚的瓜瓤,便是满嘴的如蜜醉人的香甜。红沙瓤的西瓜,瓤口黄艳艳的籽瓜,圆鼓鼓的如肥嘟嘟的小猪娃在瓜秧中趴着,摘个下来,手一拍两半,偿一口顿时一缕甘甜沁入心肺,解渴防暑,是极佳的首选。这就是那用艰辛与生命铺出的沙田结出的慰人心灵的收获。旱沙瓜,名不虚传。因为砂的保墒效果很好,凡在沙地种出的不管是翠绿的香瓜,还是金黄的黄河蜜,铁蛋子,金蛤蟆,但凡老天能给上几场透雨,这里成熟后的瓜便就有了与众不同的味道。可惜近年来,因品种的退化,人们急功近利的心态,化肥农药的过量施用,优质上等的瓜类品种少之又少,几乎成了风毛麟角,更因为经济收益的差距,从前此地优质的和尚头小麦等粮食作物几十年再无人耕种。以致于好多三四十岁以下的年轻的农民(暂切还算吧)很多没有见过自家的田地里小麦,糜子,谷子等五谷粮食是怎样生长,怎样收割,怎样打碾。地里的茄子,辣椒,蕃瓜,西虹柿,豆角等蔬菜,每家的地头上都有不错的长势,那完全是自给自足自家食用,或者留给城里的亲友们分享食用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兴水利,国家划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里的人们在付出了辛苦与汗水,甚至用生命为代价,历数年,劈山钻洞,筑坝修渠,引水上山,修建了水力灌溉工程,在运行发挥了数年的灌溉效益后,因时代所变,集体经济瓦解,无人重视,无人管理,被盗窃破坏殆尽,成为一个失败遗憾的记忆。地就仍然是铺沙的旱地,也就有了名至实归的旱沙瓜。
近几十年间,因河沟地貌数度的自然改变,河沟中流淌的泉水早断了踪影,到处是泛起的白色咸土。甚至淘挖的井里也没水出来。只有几个外来的私营工厂时不时的排出的散发出恶臭的污水和夏天偶尔暴发的山洪从沟中流过。好在这几年政府加大了农村生活基础条件的治理改善,污水排放没有了肆意的猖狂。自来水数年前就通到家家户户,早些年安装的村村通卫星电和有线电视这两年己被宽带网络取而代之,在古道的沙土路基础上,政府重修乡村公路,又恢复了一点南下北上的交通要道原有的功能。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脚下的曾经记忆中自然形成的,随着每一场山洪流过就改变线路,不断变化的沙土路,现在基本稳定的水泥路,确确实实是一条被掩没于岁月长河中的古丝绸路的一段,是自古以来兵马粮草的必经之路。一九四九年我人民解放大军的一部,就是经此处一夜的休整后,精神抖擞的沿着这条路,继续追击由此溃逃的马步芳残匪,继而解放更广矛的祖国大地。上岁数的老人们记忆的深处还留有从前驼铃铛锒的响声,马车,驴车驶过的吆喝声和清脆的马鞭声……

从古至今,这条路不知留下了多少骑马座轿,南来北往商贾行人,贩夫走卒的足迹。
沿着古道继续往北,过水源村,翻山越岭,便可下联宁夏,上达津京,北通大漠,远抵西域,谁也说不清楚多少年多少代,多少故事与传说都在这古道的历史云烟中散去!此处村庄,距省会兰州只有十来公里之远,沿古道远行而来的,不管是进城办事的还是公干的,或是经兰州继续前行的人们,大多在此住上一晚,休整一番,养足精神,梳洗打扮,面貌一新后,向城里进发,带着到达目地的欣然。继续远行的,怀揣着漫漫征途的忐忑。由此,这里便有了供行人留宿的车马店,饭馆,商铺,也就有了遗留下来的“马家铺子",“张家场子”等带有商业信息的地方的名子。也就有了做醋的,做酱的,做盐的维持生机小商小贩谋利以生的机遇。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国家建设日新月异,包兰铁路穿村而过,喷着浓烟,发出轰隆隆巨响,震颤着大地的蒸气机车便南来北往日夜兼程,为奋发图强的国家建设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一直到本世纪初,轰隆声响,喷着浓烟的老式蒸气机车被速度更快,运力更大的电力机车所取代,为国家建设货运南北,客送东西的奔驰如飞到了现在,发挥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新建的国道公路解放后改修于别地,从黄河边经水源沙沟而过的古道,曾经的的热闹便渐渐寂寞了,记忆与传说便随着一辈一辈远去的先人们的背影消失而去。路只剩下村民进出的唯一功能,村庄也就成了半封闭的村庄。
改革开放,国家大政方针调整,水源村的人们,听从党的号召,顺应时代变革的历史洪流,抓住时机,在勤劳中探索,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在几十年苦干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发展传统经济作物种植,在政府的扶持下,将水源村打造成了有名的甜瓜基地,村民的生活在衣食住行各各方面的变化正可谓地覆天翻,有目共睹。尤其是最近几年,翻建的标准化小学窗明几净,新修的道路车来车往,新装的太阳能路灯让夜晚的乡村一片明亮。村民盖起了楼房。光纤通天下,网络联世界,人们出行从前靠驴车,自行车,步行,现在除火车,乡村公交,私家骄车已成主要交通工具。尤其是年轻一代,其思想与行动与这个现代化的世界已毫无违和之感。
农闲的时候,大部分闲下的人都出村打工了。健身广场上音乐响起的一刻,便看到跳舞的妇女们姹紫嫣红的身影,朝阳而聚者,抽着烟闲喧的,是年长的人们在下棋打牌中展现出的闲散舒畅。年轻的一代用他们的所学之长,努力追求创造着更好的生活而不至于被这个社会淘汰,为自己为家庭改变着命运,为社会做着贡献。外出打工谋生的,学成在外创业发展的,虽然对土地沒有了先辈们安身立命的感情,人在他乡,但对这个养育自己长大的山沟沟,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在他们每个人的心中,渐行渐远的岁月,总有无法排遣的乡愁……
现在随着城市的扩张,水源村已被划入大城区的范筹。开发商的脚步在踏进这里停止了六七年后,因为政策的变化和投资环境的完善,2020年新冠疫情初步缓解的下半年,两个大的开发项目同时被启动。以包兰铁路为界,西面的称“万福城”,东面的名“黄河新城”。一样的大张旗鼓,声势浩大,一样的圈地数万亩。只不过不知道实力究竟如何?
村民们在被征占中盼望着,又在对补尝的不满中诅咒着,在参与中阻挠着,在同意与反对中矛盾着,心挣扎着,身疲惫着。道听途说的消息真假难辨,人们都在等最真的官宣结果。大大小小的领导与大大小小的老板们,乘坐着大大小小的车辆来来往往,与被征地的村民们在争议与妥协中,在灵活与原则中,获取着各自的利益,实现着各自的目的。
政府要政绩,商家要利益,百姓要权益。矛盾是无法避免的。这是村民,商家,政府之间为各自利益而进行的一场搏翼。这是旧事物的消亡,这是新希望的开启。新旧交替的时刻,尤如新生命诞生时的疼痛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事关祖祖辈辈,子子孙孙生活与生存悠关的变化,是自然环境的变化,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与重组。原有的农耕生活随着田地的失去,将无影可寻,取而代之的是更新,更先进,更强大的思想与文化及整体的更加文明的社会形态。
新旧交替,振荡必然。
无人机在天上飞着,人们不知道它被何人操控,为何而来?当上水头庄黑马驰沟口被开发商才开出一条车辆机械上山的路,五社下水头庄刘家沟复工后数天之内便已将一座山头几乎铲平,继而以“万福城”商住区的项目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开盘造势。
这是恒古未有的巨变时代,
在这个星球上与生具有的,在这个地方矗立了数亿万年的数平方公里内高低大小的山峦,即将在如蚂蚁搬家的渣土车的飞驰中消失殆尽。在黄尘漫天的飞扬中,在沒日没夜的机械轰鸣中,一座座山将变成一片片平地,一幢幢楼群,一条条街道,一个个社区,出现学校,公园,商店,影院,花坛……
同时依附于她怀抱里的古老村庄也将消失!那些祖辈们生存过的土地,祖先的坟茔,曾经生活的窑洞,祭拜的庙宇,寒冬里的热炕,新建的房屋,还有那闻名遐迩,香甜如蜜的白兰瓜,那翠绿如玉的香瓜,那红沙瓤的大西瓜,水淋淋的萝卜,黑油油的茄子,如小小红灯笼的西红柿都将与已经成为记忆中的石磨,石碾,圈里的猪,拉车犁地的骡马,山坡上移动的羊群,报晓的雄鸡,看门的狗,山中的兽,最终都将成为人们的回忆与后来的人们口中传说的故事。最重要的是基于以上为载体的乡邻乡情也将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土地沒有了!
变化开始了!
都市的繁华来了!
乡村的宁静沒了!
风里的歌声还唱着:
生来山里人
野菜食亦香
曾闻山外雅堂大
破衣难登它
井底说天大
芝麻当西瓜
粗茶淡饭养活咱
听风唱野花
山人自题
山,即将不存!
村,必获新生!
愿我的山村,凤凰涅槃!
愿我的乡亲,富足康宁!
耘耔
2021年元月于水源山居